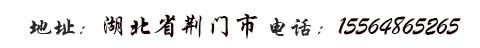短篇小说梨园里的秘密
|
得了白癜风能治好吗 http://pf.39.net/bdfyy/ 山羊在我眼前不停的晃动,他的手摇了又摇,手臂上裸露着一条条青筋,血管鼓得很高,干巴巴的,让人很容易想起一条干枯的梨树枝。山羊说:“我说的是真的,不信咱们去看!” 我和铁牛正在下五经,铁牛眼看就要输了,急得满脸通红,也许山羊地晃动使他的手气更加不顺,犹豫不定地落下一个子,被我毫不迟疑地吃掉了。铁牛赌气站起来,气乎乎地说:“不下了,走,咱们跟山羊看看去!”我说:“要去你们去,我还要割草。”铁牛说:“割个球,回来再割嘛,走!”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跟着他们向梨园走去。 日头还很高,它把麦苗子都晒黄了,无精打采的昂着脑袋,看来再过几天就要收了。棉花正长得好看,嫩嫩的,舒展着碧绿的叶子,也是在日头下静止不动。不过它们不怕热,眼看着钻新叶呢。山羊在我和铁牛的中间,向我们不断重复着他的见闻。山羊十分兴奋,血气都挤到脸上去了,象熟透了的茄子。他的唾沫乱飞,冲着我和山羊不断地发起攻击。山羊压低声音说:“他们光着屁股搂在一起,秦寡妇还嗷嗷叫呢!”看山羊的样子不像撒谎,他把手攥紧,在我和铁牛的眼前晃了晃。山羊说:“操!那才叫过瘾!” 梨园里更加闷热,我真后悔和山羊来到里面。鸡蛋大的鸭梨有点发黄,好像发育不良似的。我摘了一个放进嘴里,涩的舌头发麻,赶紧吐了,那种青涩的味道使我不住的反胃。再往里走,鸭梨都套上袋子,一个个吊在梨枝上,好像无数个眼睛,看的人心里发麻。梨园里很静,我们的脚步声都听得十分真切,偶尔一两声虫鸣打破宁静,也是匆匆而止,随后没有了声息。铁牛板着脸不做声,看来他也后悔进来了,山羊的兴致有所减弱,只顾往梨园深处走。我觉得口干舌燥,叫住山羊:“你真看见了么?”铁牛也转过头来:“你可别骗我们,小心吃拳头!”山羊又一次兴奋起来,他伸手打了一个套袋的鸭梨,袋子掉下来,摔烂了里面细嫩的小梨。“骗你们就是这种结果!”我们不再说话,继续跟随他前行。 快到一个破旧的看梨用的土屋前,山羊向我们“嘘”了一声。我们放慢脚步,象一只只野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向土屋靠近。来到土屋后面,我们都趴在一株老梨树底下,静听里面的结果。一切都静悄悄的,除了我们三个人的喘气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山羊有点着急,他越过我和铁牛,慢慢地爬到前面的窗户底下向里面观看,这一看不要紧,山羊一下子泄了气,象打蔫的茄子一样坐在地上。铁牛站起来,跑到山羊面前冲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人呢?怎们不见了,你拿我们寻开心吧?”山羊说:“不对呀,刚才还在这里的,怎么现在没有了?”我不想听他们的争论,跑进屋里凉快凉快。屋里很干净,看来经常有人来,不过这个时候的鸭梨还不需要看守,谁来这里打扫呢?在半截土炕上,我看见有一窝干草,摆得平平的,好象有人在上面打过滚。我对他们说:“你们来看,这是什么?”山羊和铁牛都气乎乎地进来,他们的争论还没有结果。山羊一看土炕,眼睛里放出光芒:“他们刚才就在这里折腾来着。”铁牛也看了看土炕和上面的干草,呸了一口唾沫说:“我们来晚了!” 从梨园里出来,我们个个无精打采,我的身上让梨园里的小虫子咬了几个疙瘩,痒痒的让人发慌。我们早没心思割草了,背起草筐向梨花镇走去。草本来割的不多,却觉得草筐很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路过秦寡妇门口,秦寡妇正坐在门前洗衣服。那是一件蓝底白花的衬衫,秦寡妇不停地揉搓着它,把水盆里的水都溅到外面来了。山羊趴在我的耳边说:“刚才她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泥鳅叔还说漂亮来着。”山羊的眼睛里放火,我赶紧避开了他。 爸爸满脸蜡黄,躺在炕上不说话。在外面熬药的妈妈一个劲地唠叨:“谁叫你大热天给梨树打药,中毒活该!”爸爸懒得搭理她,转过身去了。我把草筐放下,妈妈一看草筐,又冲着我来了:“整天疯跑,割筐草又不是要你的命!”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和妈妈争论,那样她的话就会象放机枪一样一连串的跑出来,让人没有还嘴的机会。她说了两句,见我们都不说话,也就沉默了。熬药的火一会着了,一会又灭了,浓烟在院子里弥漫,呛得人只想流泪。 大门在响,有人来了。妈妈慢悠悠地站起来,跑到门口问道:“谁呀?”说着把门打开,一见,是泥鳅叔。泥鳅叔黑不溜秋,瘦瘦的,象个干瘪的梨核。他对妈妈说:“嫂子,我来还你家的草药罐子。”妈妈把他让进院子说:“你这人也真是的,不是和你说了嘛,药罐只准借不准还,药罐你尽管使,这不,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正给二球他爸熬药呢。”泥鳅叔问:“咋,二球爸怎么了?”妈妈本来有点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她说:“大热天给梨树打药,中毒了!”泥鳅叔说:“哦,是这样啊,以后可要小心点,有一次我就中过毒,难受着呢!” 妈妈往药罐底下加了把火,烟气又一次蔓延开来,把泥鳅叔本来就黑黝黝的脸庞熏得更黑了。妈妈问道:“弟媳妇咋样了?”泥鳅叔叹了口气,“还那样,吃了好多药,总不见起色。”妈妈就说:“慢慢来吧,咋说也是个活人不是?”泥鳅叔连忙点头,转身要走。妈妈把药罐递给他:“你尽管用就是了,什么时候弟媳妇的病好了,你把它摔碎了就行。” 关上门,妈妈坐在药罐前叹气。夜色黑了下来,屋檐里的蝙蝠慌慌张张地撞出来,在夜幕中不停的兜着圈子,象一只只黑色的眼睛。我洗完脸,帮妈妈把熬好的药端进屋里,倒在碗里让爸爸喝下。妈妈问:“好些了吧?”爸爸坐起来,吐了口唾沫说:“行了,明个就能下地干活了。”妈妈说:“再歇一天吧,好好养一养,这几天又没什么事。”妈妈说完,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黑暗压了下来,装满了整间屋子,热气笼罩,让人透不出气。我觉得脊背上的汗珠流了下来,怪痒痒的。我打破寂静说:“今天山羊看到一件事情。”爸爸妈妈对我的话满不在乎,继续沉默。我继续说:“他看见泥鳅和秦寡妇在一起。”妈妈把脸凑过来,我隐约的看见她一脸惊讶。妈妈说:“可不许乱说,你们小孩子什么也不懂。”爸爸干脆向我摆了摆手:“去去去,睡觉去!”我不情愿地站起来,这么闷热,谁能睡得着呢?我抹黑向我的那间小屋走去,不小心踢倒了一个马扎,咚的一声划破了黑夜。我看见爸爸一双忽闪的眼睛。 热。热。热。太阳把一切都晒得无精打采的。梨花镇沉寂在浓浓的火浪里,燥烈得让人窒息。大人躲在家里乘凉,我们则跑进梨河里,泡凉水澡。山羊的水性不好,不敢往深水里去,只是在河边不断地徘徊。铁牛喜欢扎猛子,一头扎下去,能在水里待一袋烟的功夫,他在水里成了一条鱼。我只会狗刨,来来回回地游上几遭算是过瘾。天气一热,河水也热起来,惺气蒸腾,熏得人直想吐,我们只好跑到小树林里乘凉。山羊说:“依我看,咱们别再在这里坐着,应该到梨园的老屋里去,泥鳅和秦寡妇肯定会去的,我们来个守株待兔!”铁牛说这样也好,省得在这里无聊。 梨园里闷热,密不透风,并且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蔓延,使人的脑袋发胀。老鼠慌慌张张地跑过,刺猬在暗处吱吱地发笑,一只兔子横冲直撞眨眼不见踪影,两条蛇缠在一起交配。铁牛拿起一块干硬的土坷垃一甩手飞了出去,把一条蛇的脑袋砸扁了,露出鲜红的骨头茬子,另一条吓得仓惶而逃。梨园就是这样,掩盖了太多的秘密,每一片梨树叶子、每一块土坯底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小圆洞里都让人猜不透它们到底隐藏了什么。若是一个人的话,我绝对不敢贸然走进梨园,这里面有无数双眼睛,穿透了我的身体,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只是感应到它的存在,却看不到它。那是一种力量。 土屋这个地方比较宽阔,梨树少一些,还能觉察出有一股凉风。我们进了屋子,竟觉得屋子里凉飕飕的,很舒服。山羊往土炕上一躺说“真爽!”铁牛也跑过去躺了下来。外面寂静,只有唰唰的响动,那是梨树叶子在摩擦。我们觉得很无聊,又不愿意出去,只好呆在屋子里打发时光。日头高高地升起来了,没有了风、声音、还是不知名的虫子。一切压了下来,整个梨园就有了一种空荡感。寂静有时候是可怕的,就像这偌大的梨园,没有了声音仿佛就没有了生命。 脚步声。我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进,而且很沉重,这肯定是一个男人的脚步,我可以听得出来。那是一种喘息、笨重、缓慢和小心翼翼。我看了看山羊和铁牛,他两个人已经睡着了,山羊的嘴角流出一股清亮的口水,粘在炕上的野草上面。脚步声离土屋越来越近了,我轻轻地把他们摇醒。山羊一个激灵,他顾不得擦去口水,向我和铁牛“嘘”了一声:“来了!”我们屏住呼吸。这时候,脚步停止了,然后一声咳嗽。紧接着,我们看到了泥鳅佝偻的身躯和他的半边脸,他的脸通红,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我们使一个眼色,一下子聚到门口,吓得泥鳅连连倒退了几步。 “泥鳅叔,大热天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山羊不怀好意地问。泥鳅向四周瞅了瞅,长长地嘘了口气说:“吓我一跳,你们仨在这里干什么,要偷梨吗?”山羊一下子让泥鳅给问住了,支吾地说不出什么。铁牛说:“这时候偷梨干什么,又不能吃,我们到这里来凉快。”泥鳅哦了一声,直了直腰板对我们说:“我来寻点婆婆丁,给你们婶子下药,你们玩,这里好像没有,我到别处看看。”不等我们答话,泥鳅一转身钻进梨树空子里,不见了。 山羊懊恼地坐在地上不做声,铁牛也板着脸站在那里,我问:“还等吗?”山羊站起来,懊恼地嘟囔了一句:“让泥鳅叔给发现了,还等个屁,走吧!”铁牛也说:“别等了,咱们还是回家睡觉去吧,这梨园里怪闷人的,静得让人心里发虚。”我们按照原路返回。这时候的梨园都静了下来,密不透风,枝干遮住了太阳,洒在地上的,只是斑斑点点阳光的碎片。我们在树枝间穿梭,把碎片也给打乱了,成了晃动的光点。 走在梨花街上,我们三个人只是一个圆圆地黑点,太阳让我们把自己踩在脚下。刘燕巅巅地从梨花街那头跑过来,她一蹦一跳的,手里还举着一块雪糕。刘燕是泥鳅叔的女儿,和我们一般大,小巧玲珑,和泥鳅叔一样,细细的,灵巧得象一只燕子。铁牛向我们使了一个眼色,我们便在街上并摆开来。刘燕走到我们跟前停住了,她狐疑地望着我们,把高高举着雪糕的那只手放下来,问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怎么不回家?”铁牛没有回答她的话,两只眼睛盯着她手里的雪糕。刘燕明白了,连忙把雪糕藏在身后。铁牛凑近了一步问:“燕燕,你手里拿的什么?”刘燕怯生生地说:“雪糕……”铁牛更加恬不知耻地向前一挺身子:“让我们偿一口!”刘燕连连倒退,“不行,这是我才买的。”铁牛冲着我们一摆头,我们便象影子一样跟了过去去抢,刘燕挣扎着,并且把雪糕攥得紧紧的,就是不撒手。铁牛说:“我们就尝一小口嘛!”伸手也去夺,结果,由于用力过猛,雪糕没到手就掉在地上摔碎了。刘燕蹲在地上哭了,她的声音在梨花街上蔓延,拐弯抹角地飘散开来。一见刘燕哭了,铁牛也就陪她一起蹲在地上。“不就是一块雪糕嘛,值得你这样?”刘燕边哭边说:“我是给妈妈买的,我看见她热,浑身湿漉漉的,就把攒着买作业本的钱给她买块雪糕吃,结果让你们给遭踏了……”刘燕哭起来脸就涨得发红,眼睛水灵灵的,就像井水一样清澈,怪不得人们都说她和泥鳅婶象一个模子里刻的。铁牛站起来说:“我们赔你一块就是了,你先回家,我们买了给你送去。”刘燕抹着眼泪,哭哭啼啼地走了。 铁牛站起来,翻了翻口袋,他的口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他看了看山羊,山羊连忙把口袋也翻了个底朝天,“我可没有钱啊!”山羊无奈地看着铁牛。铁牛的脸黑了下来,我知道他很要强,答应了的事情绝对算数。我的口袋里还有五毛钱,那是给爸爸买药时我私自克扣下的,我想攒着它买只圆珠笔的。我掏出钱,递给铁牛说:“我有五毛钱,咱们去买吧。” 雪糕三毛钱一只,看我们三个人,小卖部的墩子叔就给了我们两块。一块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口吃掉了,另一只铁牛抓在手里,仿佛一不小心会掉在地上一样。刘燕家在梨花街的西北头,我们飞快地向她家跑去,生怕雪糕化了。刚进刘燕家门,一股浓浓的草药味就钻进鼻子里,冷不丁地让人喘不过气来。刘燕在院子里熬药,烟气呛得她在那里咳嗽,眼泪也哗哗的掉下来。见我们来,她笑了,热情地叫我们坐,仿佛把刚才的事情忘掉了。铁牛庄重地把雪糕递给刘燕,“燕燕,这是婶子的,我们拿给她吃吧。”刘燕笑了,灿烂得象院子里的向日葵,她向我们一招手,我们便跟在她的身后进了屋。潮湿、昏暗还有莫名的味道占据了整间屋子。泥鳅婶躺在土炕上,象木头一样,直挺挺地在那里,让人的心里增添出许多恐惧来。那年,她被一辆汽车撞了,汽车跑了,她却差点没命。抢救了一段日子,泥鳅婶就成了植物人,在炕上一躺就是好些年。梨花镇的人都说,泥鳅婶不如死了好,这样对自己是一个解脱,对泥鳅叔和燕燕也是解脱。可是,泥鳅婶没有死去,依旧不言不语、一动不动的活着。透过昏暗,我看见泥鳅婶灰黄的脸,没有一丝血气,象腊一样凝固在哪里,若不是她在慢慢地眨眼,我们还真以为死了呢。刘燕把雪糕放在泥鳅婶的嘴边,融化了的雪水慢慢地滴到她的嘴里,仿佛,她的嘴角还抽搐了一下。刘燕转过头来对我们说:“我妈笑了,你们看。”“笑了吗?”山羊问。刘燕兴奋地说:“笑了,笑了,我妈真的笑了!”我看见泥鳅婶的一双眼睛里仿佛溢出了一丝泪水,在昏暗的小屋里显得有一些晶莹。我对山羊和铁牛说:“笑了,我看见她笑了。” 刘燕家的院子很大,种满了向日葵,现在刚刚开花,香气和药味掺杂一起,让人猜不透是什么味道。蜜蜂嗡嗡,在花瓣上穿梭不止。我们玩了一会,太阳就偏西了,仿佛还有一丝凉风。铁牛说:“我们该去割草了,要不然又要挨骂。”我们跟着他出来。我的脚迈出刘燕家门口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泥鳅婶说:“再坐坐吧……”是她说话吗,她能够说话吗?我怀疑听错了,站住脚步。铁牛问:“愣在那里作什么?”我说:“你听见什么了吗?”铁牛头也不回:“没有!”我想,那一定是泥鳅婶的灵魂在说话,她太寂寞了。 寂寞使人迅速老去。 夏天会使一切疯狂,刚刚收了麦子种上玉米,一眨眼功夫,玉米就半人高了。浩浩荡荡地立在地里,象深绿色的波浪。当然,没有风,它们照样显得死气沉沉,好像定在那里一样。知了恬不知耻地嚎叫,变换不出两样的调子,吵得人烦躁不已。天色一黑,铁牛和山羊就过来约我了,我们到梨园里去逮知了牛。知了牛可以炸了吃,也可以卖钱。我们逮了舍不得吃,大多卖了钱。这个钱爸爸妈妈是不会要的。我们把钱攒起来,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个时节在梨园里要小心行走,要不然会把小梨碰下来,或者被梨树枝碰了头。我们一般在近处游荡,不敢往深里去,那里面太黑,黑洞洞的令人胆颤心惊。 山羊似乎对知了牛不感兴趣,他昂着头不看树枝,而是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吹着口哨。我听出他的口哨很急躁,老是嘎然而止,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我说:“山羊,你别吹了好不好,怪瘆人的。”山羊就转过头来对我和铁牛说:“咱们去老屋子吗?”铁牛看到了一只正往树上爬的知了牛,逮了过来,他说:“要去你去,我不去,那里面有什么好看的?”山羊哼哼一笑:“我就知道你们不会去的,都是胆小鬼!”铁牛攥紧了拳头在山羊脸前晃了晃,“去就去,谁怕谁!”我知道铁牛中了山羊的激将法了,可是又不好说出来,只好跟着他们向梨园深处钻去。 一切都静了下来,静得出奇,我们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套了袋子的梨象黑色的眼睛,闪着幽光,有一种冰冷的感觉。我觉察出自己的冷汗正顺着皮肤向外渗。快到老屋时,我们停住了脚步。透过树枝和树叶看过去,老屋那里坐着一个人。我们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是,他嘴里的烟火在一闪一闪。我说:“是不是鬼呀?”山羊小声地说:“哪里有鬼,鬼会抽烟吗?”铁牛不说话,撩开树枝走过去了。我知道,他想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呢。那个黑影站起来问:“来了?”说着,向铁牛迎了过去。 铁牛说:“谁呀?”那个黑影站住了,紧接着,猛然转过身,一压腰,钻进梨园跑了。铁牛向我们一招手,大喝一声:“追!”我们跟在铁牛身后,在梨园里飞快地穿梭。小梨让我们碰掉了,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这个响声在我们的身后不断地传来。那个黑影在梨园里来回拐弯,不一会就不见了。铁牛气喘吁吁地说:“算了算了,我们追不上了。” 我们回来时,夜已经很深,人们都回屋睡觉去了,整个镇子恢复了宁静。狗在远吠,有一声无一声的,也睡着似了。知了牛都变了,在我们的盒子里脱了皮,这些得自己吃了,一个晚上的功夫白费。铁牛和山羊一路沉默,可以猜测他们的脸色肯定不好看。我觉得心里很痛快:谁让你们到老屋那里去呢? 快到秦寡妇的门口时,我们看到一个人躲在她的门边。我们赶忙止住脚步,躲在暗处。那个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开了,他象猫一样闪了进去。 那是谁?这个疑问在我们的脑子里转过来又转过去,成了一只虫子,搅得脑袋痛。山羊说那肯定是泥鳅叔,只有他才会到秦寡妇家里去。铁牛则说不是,梨园里的应该是泥鳅叔,那个声音像。可是,他冲着和秦寡妇家相反的方向跑了,这时候不可能回来。那么,进秦寡妇家的到底是谁呢?我们想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最后,铁牛很不耐烦地说:“走走走,回家睡觉去,管他娘的是谁!”我们各自回家。 我们都愿意和刘燕玩,她在家里照顾泥鳅婶,不能出门,我们就到她家里去。泥鳅叔不说话,沉着脸坐在门槛上抽烟,门洞都让烟气给熏黑了,他的咳嗽震飞了墙头上的麻雀,惊慌失措中抖落一地羽毛。他偶尔朝屋里看一看,也只是叹气。泥鳅婶这一阵更瘦了,或许是天热吃得少的缘故吧。她干巴巴地躺在那里,纹丝不动。过一会,泥鳅叔就过去翻动一下她。泥鳅叔把她抱在怀里,像抱一捆麦草那样轻巧。刘燕每天都要熬药,她的脸都熏成草药的颜色了,红里透着青。山羊鼓着腮帮子帮刘燕吹火,浓烟就飘散开来,整个院子荡漾在熬药的气味里。铁牛帮刘燕添柴,往往压灭了刚刚升起的火苗。烟气更大了,我们四个人便守着药罐子流泪。 每次泥鳅婶吃药,总是泥鳅叔亲自喂她。泥鳅叔把泥鳅婶揽在怀里,让她昂着头,然后一小勺、一小勺慢慢地让婶婶喝下去。泥鳅叔的动作缓慢但又轻巧,这和他很不搭配,就像一位害羞的女人。泥鳅婶从不张嘴,药顺着嘴角慢慢地灌下去了。泥鳅叔够有耐心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精心呵护着泥鳅婶,这才使她活了下来。泥鳅叔也许相信奇迹,或许有一天泥鳅婶会好起来。可是,奇迹是不容易发生的,那只是巧合罢了,在绝望中守侯着希望,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刘燕和我们说:“爸爸总是和妈妈在屋里说话,他说话的时候不让我进屋,也不让我听见。”山羊闪着眼睛:“那是大人们的悄悄话,我们小孩子不能够听。”刘燕说:“可是,现在爸爸和妈妈说话的时候少了,他老不在家,每天回来得很晚。”山羊说:“也许上梨园了吧?”刘燕问:“到梨园干嘛?”铁牛就说:“收拾梨树,梨长多了好卖钱。”铁牛瞪了一下山羊,山羊就低下了脑袋。刘燕说:“怪不得呢,其实爸爸很辛苦,每天下地做活,晚上还要喂妈妈药。唉,等我长大了就好了,也能帮爸爸一些忙。” 我站起来,看了看被烟气熏得昏暗的天空说:“燕燕,你已经长大了。”我们都站起来对刘燕说:“是的,你已经长大了!”泥鳅叔从屋里走出来看着我们,我们不说话,而是噗哧笑了。这时候,药罐底下的火突地燃烧起来,映红了我们的脸。 秦寡妇和六指在一起。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六指和秦寡妇在一起,反正他两个在一块了。在秦寡妇的梨园里,六个手指头的六指正帮她摘梨。六指那只多余的手指长在他的右手上,就像一个脚指头一样,短小而又精悍。六指的手还是很灵活的,他摘梨的速度非常快,两只手轮流着在梨树枝上游动,一个个鸭梨就被他摘下来了。秦寡妇跟在他的身后,接过梨,然后轻轻地放进梨筐里。 六指从小光棍一个,好吃懒作,经常饿得两只眼睛闪着蓝光。据说他找不到媳妇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懒。镇上的人说,就算六指的手是正常的,照样讨不到老婆,谁愿意嫁个懒汉过日子呢?前几年,六指的爹娘先后死了,死的时候都张着嘴瞪着眼,满肚子遗憾带到阴间里去了。爹娘一死,泥鳅更加的懒了,连饭也不做了,而是四处游荡,看到谁家下地,他就跑过去帮忙。别看六指在自己家里懒,在帮助别人做活时,那可有使不完的力气。做完活,人家过意不去,请他到家里吃饭,他也毫不客气,吃个嘴饱肚圆。幸运的话,还能混上一两顿老酒。用六指的话说这叫神仙生活。 以往他从不给秦寡妇做活的,这次怎们凑到一起了呢? 梨花镇的梨园是连成片的,那是梨树的海洋,到了摘梨的时候,人人都会来到梨园里,摘梨、卖梨。我家的梨园经过秦寡妇的梨园,从她的梨园路过时,就看到他们在一起。六指用那只六个手指头的手把梨递给秦寡妇时,还不时的摸一下秦寡妇的手。我看的真真切切,六指嘿嘿地笑着,他的那个多余的手指因为秦寡妇而欢快地跳跃。秦寡妇也不在意,继续接梨。我和爸爸说起他们的事情,爸爸说早就看见了,那有什么好奇怪的,孤男寡女难免会出一些事情,况且他们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光棍,正好一对。妈妈结过爸爸递过来的梨说:“那个秦寡妇呀,这是何苦呢?”爸爸不耐烦地说:“人家愿意关你屁事,接梨!” 山羊家的梨园在左边,铁牛家的梨园在后边,我们三家的梨园成了一个三角。我们没有心思摘梨,而是想着如何凑到一起,相互递着眼神。山羊冲着我和铁牛眨了眨眼,然后看了看不远处摘梨的泥鳅叔。泥鳅叔摘梨的时候黑着脸,我想,他肯定看到六指和秦寡妇在一起了,心里在生暗气。可是,生气又有什么用呢?刘燕小心地接着梨,低头不语,好像在想着心事。爸爸从梨树上下来,叫住摘梨的人们:“过来歇一歇呀!”人们慢慢地聚拢过来,坐在一起。泥鳅叔最后走过来,坐在爸爸对面。爸爸把烟递给他,然后相互点着了。我不愿意闻烟味,约山羊和铁牛跑过去找刘燕玩。刘燕的脸红红地,上面沁着细细地汗珠,气喘吁吁地坐在梨树底下。我拿起一个梨给她,她说刚吃过,我就自己咬了一口,梨水很多、很甜,还有一股梨花的味道。刘燕说:“这一阵我妈的病很厉害,吃药都不管用了。”刘燕一脸忧愁,像刚刚盛开的梨花上面洒落了雨点一样,柔弱不堪。山羊坐下来,对刘燕说:“没事的,泥鳅婶会好的。”刘燕点了点头,拾起一片叶子仍了出去,叶子很轻,飘出去又慢悠悠地飘了回来,落到她的脚下。叶子黄的有些发红,脉文清晰可见,给人一种衰败的恐惧感。我想把它拾起来,却发现满地都是,浩浩荡荡地摆满了整个梨园,就像着了火一样。风一吹过,火苗就窜到人的脚下了。 泥鳅叔的梨摘完的时候,秦寡妇的梨摘了一半。六指已经大汗淋漓了,湿透了的衣服贴在他的背上,显露出了干瘦的脊骨。不过六指照样乐呵呵的,他的脸上露着兴奋的光芒,在夕阳里发着红光。泥鳅叔默默地走过去,他的身影在夕阳里呈现了一个优美的弧度,让人很容易的想起一条长满了梨而压弯了的树枝。他默默无语,以倔犟的神态为秦寡妇摘梨。我想,我应该帮忙,至少我不愿意六指和秦寡妇在一起。我冲山羊和铁牛打了一个尖尖地口哨,他们就随我过来了。我来到六指身后,把秦寡妇挤到一边去了,然后伸手接梨。六指把梨递到我的手里,还狠狠地摸了一下。我哈哈笑了,六指一见是我,连忙说:“你,你怎么来了,那谁呢?”我说:“谁,谁,谁呀!我怎么不能来,我也来帮忙啊!”六指着急了,着急了的他说话就有点结巴:“小孩子家帮……帮什么忙,去去去,一边玩去吧!”他的话我们根本不放在心里,我们凭什么听他的。一见我们帮忙,秦寡妇就跑到泥鳅叔那接梨了。泥鳅叔摘梨很慢,好像梨都很沉一样,然后缓缓地递到秦寡妇的手里。秦寡妇犹豫,泥鳅叔就强行把梨放到她的手里。六指急得出汗了,想从梨树上下来,我们三个就把他围住了。山羊说:“快摘呀,快摘呀。”山羊的口气里带着轻蔑,叫得六指手忙脚乱,手里的梨扑通掉在地上,摔碎了。山羊就说:“怎么干得活,真不行!”六指就说:“怎么不行,怎么不行,刚才那是失手!”失手刚一出口,六指就失脚了,一脚踩空,整个人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幸亏有树枝挡住。我们哈哈地笑着,整个梨园也就黑了下来。 六指被我们气跑了,他一瘸一拐的,两只肩膀高低起伏。我们冲着他吐唾沫,唾沫落下去,掉到红红地叶子上。刘燕早早地回家了,她要早早地把药熬好。我们和泥鳅叔帮助秦寡妇把梨送回家去,秦寡妇感激得很,非得留下我们吃饭。铁牛不愿意吃,早早地回家了,我也觉得在这里吃饭没有意思。看看山羊,山羊只好咽了口唾沫,跟着我走了。泥鳅叔正帮助秦寡妇生火,火苗冒出来,闪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一双发光的眼睛。 刚出秦寡妇的门,一条狗窜过来汪了一声,一看是我们,反而讨好地摇起了尾巴。山羊跑过去,一脚把狗踢蹿了。山羊对我说:“他们两个肯定有故事,要不然泥鳅叔怎么不走?”山羊自言自语,脚步有些踉跄。他站住脚,拉了我一把:“咱们再回去看看!”我还没来得及挣脱,就被他拉回来了。 我们趴在一株杜梨树后的黑影里向里观看。院子里灶火里的火冒着零星火星,上面的锅子冒着热气。她的门关了,里面悄无声息,昏黄的灯光从窗子里反射回来,让人看不清里面的事情。山羊在我耳边说:“有声音,你听。”我就把两只手拢在耳后,还是没有听见什么。山羊就说:“秦寡妇在叫唤,真的,她在叫唤。”我怀疑我的听力和山羊的听力,到底谁的耳朵灵呢? 不过,我们却共同听到了一个脚步声,我们赶紧屏声静气,等待着那个人的到来。一个人慢慢地走过来,那是六指,他像作贼似的,四处看了看,然后用那只六个手指头的手拾起一块半头砖,一甩手仍了出去。那块砖头砸到秦寡妇的门板上,咣啷一声。六指赶忙转身跑了,在夜色里,他象跳动的影子,悠悠不见了踪迹。 屋里的灯灭了。 梨花镇有两个季节比较繁荣,一个是梨花开的时候,整片梨园都白了,好像一夜之间下了一场雪一样。不过,雪没有味道,而梨花是有香气的。香气氤氲了整个镇子,人们都醉了。许多外地人前来看花,密密麻麻地在梨园里游赏。看花人有钱,他们毫不吝啬地购买梨花镇的土特产,包括鸭梨、荠菜、白萝卜还有梨木的印章。镇上的人轻松地赚了钱,喜气挂在脸上。再个就是熟梨的时候,梨贩子蜂拥而至,不光摘梨、购梨,还带来了一些风月女人,她们租了梨花街两边的旧房子,把两只雪白的大鸭梨用红头绳穿起来挂在门口,等待别人摘了去接客。镇上的人赚了钱,梨贩子赚了钱,那些女人也赚了钱。 梨花镇真是个好地方。 这两个季节过去,梨花镇的繁华热闹就兀自而落,一点声息都没有,说静就静下来了,冷不丁的让人心里不好接受。卖了鸭梨,梨花镇就空了,静了,显得死气沉沉。男人们懒得出来,在家里打牌、喝酒,偶尔赌个小钱,女人们懒洋洋地坐在门口打盹,梨叶落在身上也浑然不觉。梨园里空荡荡地,梨叶大多都落了,只剩下少数梨叶在树枝上随风摇曳。梨花镇要睡着了。 爸爸不愿意打牌,在院子里打磨他的农具,妈妈倚在院子的梨树底下纳鞋底,攥在手里的针在太阳底下闪亮地发光。门口有人走过,和爸爸说上两句话,脚步声就远了。几个人聚集起来,倚在墙根底下谈天说地,争论的声音在街上蔓延,梨花镇总算有了点生气。六指缩在墙角,他的脸色蜡黄,看来没有吃饱。地里没有了活路,他替别人干活混吃也就到头了。有女人走过,六指的眼睛发亮,不过,不一会就黯淡下去,他的肚子提醒他不能光想女人,还要搞点吃的。时间就在等待中过去。 山羊和铁牛约我到刘燕家里做作业,我背上书包跟他们走去。刘燕一个人在院子里,正在地上胡乱画着什么,见我们来,赶忙进屋为我们端来瓜子。刘燕说:“这是我自己炒的,很香。”我拨开一粒吃到嘴里,果然很脆很香。山羊问:“泥鳅叔怎么没在家?”刘燕说:“不知道,吃了饭就出去了,可能去玩牌了。”山羊就笑,他的笑挂在嘴角,没有声音,让人觉得干巴巴地,一点意思都没有。 有人敲门,刘燕赶忙跑过去,来人是秦寡妇。秦寡妇来到院子里,看到我们就说:“你们都在啊。”山羊眼里放了光,连忙站起来问:“秦婶来看我们做作业吗?”秦寡妇脸红了,她说:“我来看看嫂子,好久没看她了,怪想她的。”刘燕说:“我妈在炕上躺着,秦婶进屋吧。”秦寡妇却退回来说:“改天吧,我家里还有事,你们玩,我先走了。”说完,闪身出了院子。 山羊愤愤地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无事不登三宝殿!”刘燕就问:“什么事啊?”山羊脱口就说:“她来找你爸爸,肯定是找你爸爸,吃馋了!”刘燕不解,连忙又问:“找我爸爸干嘛?”山羊刚想张嘴,铁牛呼地就站起来了,他一脚把山羊踢倒在地,山羊呛了一脸土,鼻子也摔破了,一股血丝流出来,染红了山羊的半边脸。山羊爬起来,攥紧了拳头。一般情况下山羊是不敢和铁牛打架的,因为他打不过铁牛,不过这次他真急了,象一只恶狗一样扑上去。铁牛机敏的一躲,闪过了山羊,他一伸腿,把山羊绊倒地。我和刘燕赶紧拉架,怎么说打就打呢。铁牛气乎乎地说:“谁让他多说话了,活该!”山羊的鼻血止住了,血迹粘在脸上,变成紫色的,他指着铁牛说:“我怎么就不能说,是真话我就要说!”铁牛就说:“你再说我还打!” 刘燕一脸迷惑,他不知道山羊到底要说什么,一双眼睛眨个不停。我心里清楚山羊要说什么,不过,我不能说,至少不能守着刘燕说。 屋里有响动。这是我先听见的,我冲山羊和铁牛大声说:“别打了,你们听屋里是什么声音?” 他两个住了手,一起朝屋里看去。刘燕赶忙跑到屋里,我们也跟着冲进去。 泥鳅婶在动,说是动,不如说是跳跃。泥鳅婶的脸上起了汗珠,她的身体在剧烈摇动,她的两只胳膊在不停地摇摆,好像要抓住什么。刘燕吓得哭了,连忙问:“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泥鳅婶张着嘴,可是不说话,也许她说不出话,依旧摇动不止,她太瘦了,几乎剩下了骨头,她象一捆跳动的稻草。我们赶紧摁住她,可是她依旧晃动,我们便加大了力气。我抓住了她的一条胳膊,山羊抓住了她的另一条胳膊,铁牛抓住她的腿。 喀喳。 我听见断裂的声音。然后,泥鳅婶的那只胳膊不动了,从我得手里滑落下去。 喀喳。 山羊手里的那只胳膊也不动了,慢慢地从他手里滑落下去。然后,泥鳅婶恢复了平静,她一下子不动了,她的嘴里轻轻地向外吐气,那是一声长长地叹息。 我们吓蒙了,铁牛大声说:“坏了,泥鳅婶快不行了,我们赶快去找泥鳅叔!” 我们丢下刘燕跑出来。梨花街很静,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喘息声还有心脏的跳动声。脚步声很大,早早地传到了街头并反弹回来。铁牛说:“去梨园!”我们便跟在他的身后。幸亏摘了梨、落了叶,梨园显得有些空,我们在里面穿梭,碰落了几片红如血的梨叶,梨叶飘荡,象一个无家可归的灵魂。 快到老屋时,我们同时喊:“泥鳅叔,婶子死了!”我们的声音象蛇一样穿过去,泥鳅叔就从老屋里窜了出来,他随手穿着上衣,赤着脚向梨花镇跑去。他的脚步带起了树叶,他象踩着一团火。 我们闯进老屋,秦寡妇光着身子坐在那里。我们感到一阵耀眼,因为她的乳房象两只套了袋的鸭梨,雪白雪白的。山羊把衣服仍给她,“泥鳅婶死了,你们如愿了!”山羊气得呼呼,象一条发了怒的狼,两眼喷火。秦寡妇在那里一动不动,好久,她才哭了出来:“作孽呀,我只是找个男人啊!”她的眼泪喷涌而出,象一股泉水。她一哭,山羊就心软了,我们都心软了。或许她真的需要个男人,泥鳅叔也需要个女人,事情都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从老屋里退了出来。这时候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感觉到了温暖。梨园一望无际,缓缓地延伸到了天边。我们在梨园里穿梭,第一次感受到了梨园另一面的寂静。这是一种安详的平静。它能够让人的心里也静下来,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变得轻松无比。红红的梨叶在脚底下飘散,纷纷扬扬地象火红的蝴蝶,被风吹来在梨园里飞舞。 山羊说:“操!梨园让我忘了一切。” 铁牛说:“我也忘了。” 我说:“我也忘了,包括秘密。” 梨花镇就在眼前,它也被梨园轻而易举地围绕在里面,象一幅优美的画。我们都在画里了。 梨园真好。(作者:马卫巍)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nzizhanga.com/yzzqc/9043.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书预告新诗路bull民间诗库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