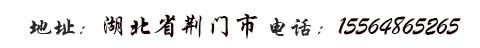高密作协苇青青散文三章
|
北京专治痤疮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yqhg/210111/8578752.html 点击上方「蓝色 水拍着岸边的礁石,拍一下,发出哗的一声响,溅起一朵、一簇或一排浪花。浪花是白色的,白得想让人揣住。浪花退去,总想等待下一批浪花的到来,看那一次次晶莹的撞击。有些礁石是光滑的,有些是不规则的。它们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有的是白色的,在阳光下,白得发亮。有的是黑色湿润的,浸在水中很长时间或很多年了。还有的,是褐色的,像一位常年蹲在岸边被晒黑的老人。岸边立着一座楼群,不用多想,就羡慕着它们每天能享受到海的沐浴。马达声传来又远去,是渔船在过往,声音从水面传出老远。 海草在浅水处摆动的样子分明看得清楚,它们的姿势被水冲向同一个方向,然后又向同一个方向摆回。水中有座小岛,远看,雾中黛色。我想象着那上面一定覆了一层绿草,不知名的绿草。我很想把岛上的绿草带回家,很想。可我登不上那座岛。只能远远地望。于是,在离开海的时候,我把礁石边的车前草,水边的海草,采一棵和一束,带回房间。水草搁置书桌上,海,就靠近了我。 3 朋友邀约去海上钓鱼,一直钓到夜里。一想就美得不行——蓝色的海面,全都成了黑色的了。如果有月光,那平静的水面,会闪动着一亮一黑的波纹。星星倒映在水里,把深秘从天上布到海底,让人即刻想伸手触摸,甚至弯腰够下去。还有月儿,海心的中央,会有一轮亮得发黄的圆碟晃来晃去。而那船只,也随着晃动的频度,摇来摇去。那个时刻,不知人在天上,还是水上,像处在一个神秘得不能触摸却又被神秘触摸着周身的仙境妙处。远处,是望不到尽头的黑。偶而有一点光亮,那是捕捞未归的船只,或许,是与这条船一样去垂钓大海的渔翁。那个时候,我会躺下去仰望星星,星星比平时高比陆地亮,有几颗大的要坠下来的样子。如果眯起眼,像一盏盏提在空中的灯笼,变成光束争相四射的一团团光。一会儿,又被慢慢蒸起的海雾弥漫。这时,我会一个骨碌爬起,俯在船体,向海中探望,望海里的星星与天上的星星相约隐去,望那一片黝黑的蔚蓝,一片无边无际的水陆。身体在船上,思绪在海上,黎明,就在东方一线射红的水面上…… 4 一种“嗒——嗒——”的声音敲在窗外水泥板上。打开窗,海水茫茫,雨正下着。雨雾中,一只鸟儿飞旋在天空,啾啾鸣叫几声,冲向更高的云层。旋即,不见了。我不知道它是北归,还是南飞。是在寻觅吗?寻找妈妈,还是同伴?抑或雨中的食粮?我立在窗前,久久凝望鸟儿飞过的地方,顺着飞去的方向,想象着雨中它怎样艰难地张开打湿的翅膀。一阵秋风,漫着海的味道,掀动洁白的窗帘。我的眼睛透过窗棂,停留在小鸟飞过的天际。下雨的日子,鸟儿该是栖息在温暖的窝里。而这只鸟,它的家在何方?我后悔刚才不早些打开窗子,如果早些时候,让鸟儿栖息在我的窗前,或栖进我的房间,为它擦去羽翼的冰凉,该是一件多么安慰的事…… 孤独的布谷鸟 这是一座四百年的村庄。村庄有一座三百年的老屋。这座老屋的久远让满院蒿草摇曳着荒芜与神秘。我是这座老屋的继承人,又是不被乡里认可的正宗传承人。按村俗,我是不应见到家堂的外人,称异姓人。虽然我实实在在流淌着老屋先辈的血脉。 我是他们的亲骨肉,但我的确不是被族人认可的那种继承人。可先辈不知为何,就那么一念之间,将老屋传给了我。 当我独自拥有一座三百年老屋的深夜,拥有一座寂静得连虫鸣都是从幽远的祖先深处传来的院子时,我真正走近了老屋——此时,从少年门槛迈出,至满载沧桑归来,已是几十年的光阴。 打开院门,一院荒草。挤挤的,满满的,密不透风,高过头顶。这是一个傍晚时分,草的颜色已黑黢黢的了。我就打算在这荒凉中住下来。这时,从院落一角传来“布——谷、布——谷”的叫声。那叫声短而哑。我想了想,秋天该不是布谷鸟活跃的季节,打哪儿飞来这样一只喑哑的布谷?我没有细想下去,只是目光掠过满院荒凉。 住下来的第一夜,我安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那只布谷鸟又在院子里叫起来,声音仍是短而哑,哑得心里发紧。这声音送到耳鼓,明明是在求救哀鸣一般,让人觉得真是一只病了的或失落家园已久的鸟。细想一下,三十年前儿时的院子里没有这种鸟,屋后的树稞子里也没有这种鸟,以至于我到了某个城市一座动物园第一次听到这种鸟鸣,兴奋地拦住同行的旅人,问那是什么鸟在叫。后来想想,这小庄人家的孩子,真是见识短浅,从人家大城市人眼光中和牙缝里挤出的“布谷鸟还不知道吗?”我已感到了自己的羞愧。我从此记住了布谷鸟的叫声,并且与这种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每到一处林子,若听到这种鸟鸣,我会追到树下或追赶鸟的飞翔,尽管布谷鸟常常留给我一条尾巴,但我还是见到了它的身影,听到了它别致的叫声。我总是欣喜地蹦出一段路。又总是遗憾着我的老家为何没有这样一种鸟。 我家院子的这只布谷鸟,它的叫声低低的,哑哑的,不像是从西墙下那棵上百年树龄而今正枯着的梧桐树上传出。倒像是从草丛深处,或从老墙一角,幽幽地发出,凄凄凉凉,不忍听和想象。布谷鸟就这样低低地叫了一阵子,沉寂了。等到第三天早上推开木窗,那只布谷鸟又叫开了,“布——谷、布——谷”一声声低哑,徐缓,叫几声,又沉寂了。傍晚刹黑时分,没有掌灯,当一天的沉思让我顿然想起用手摸向一只茶杯时,那只沉寂了一天的布谷又掀动起我的思绪。“布——谷”“布——谷”“布——谷”,声音如旧,只是,这声音越来越拨动人的恻隐之弦。只要屏息侧耳听上几声,断然听懂这叫声不是布谷欢快的鸣唱。可是,它为何一直沉寂?带着这个疑问,我与夜空下一院荒草和空寂一同睡去。 第四天早上,刚刚醒来,推开木格窗,几乎与窗子打开的同时,我又听到了布谷的叫声,声音仍旧如前,低婉凄凉,细数,整整叫了七声。这七声间隔长而缓,占用的时间超过了正常七声的时长,如果耐下心来听完,会觉得陪它走过很长一段路。这段路,总是拉向我长长的沉思。就在这样每天的同一时段里,叫声重复着。当过了三天之后,我明白了这只鸟的心思。我已确信,这只鸟是为我而鸣——是早晨迎接我,或是夜晚伴我入眠,抑或有难言的苦衷向我倾诉。我说不准。但我确信,它一定与我有关。我确信这是一只灵鸟,就住在这座院子里。而且,它有什么话想向我说。 不知是我分担了这只布谷鸟的孤独,还是我的孤独里增添了同伴的一两声低语,在这无边无际的孤独长夜中,我们达成了默契。我知道,这座古老的院落,有一只布谷与我相伴,它就在树上或草里,或墙落。它到底生存在哪个更具体的位置,我已不急于知道。但我知道在我身旁,有一只布谷的存在,这足够让我安慰。假如每天的早晨和夜晚,那只布谷是从很远的远方传来,为我而鸣,不管它身在何方,身处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幸事吗?这样想着,就打消了想在某一天拨开茂密的蒿草去寻找那只布谷的想法了。 我与布谷,一直保持着至今未能见面的声音传递。尽管这声音只有我能听懂它钻心的凄凉。时间一久,在早晨醒来或晚上入眠之时,最盼望的事,自然是想听到几声布谷的叫声,尽管那是朝向我的凄凄低语。再后来,我已更加确信,这只布谷鸟清晨叫七声,晚上叫三声。那三声之后,再侧耳,它已沉默,不会有多一声的发音。在一段时间,我曾扶窗久未挪动,我多么希望它的语言能多一些,再添一句,哪管一字。可是,布谷鸟的语言十分吝啬。终于有一天,在我居住的第七个傍晚关窗欲寝之时,那只布谷鸟在低低地用同一音色“布——谷”“布——谷”“布——谷”三声之后,我竟忍不住合着布谷同样的分贝,朝窗外“布——谷谷”“布——谷谷”“布——谷谷”连叫了三声。三声之后,我听到了一片刹那间的空寂,几乎在空寂沉过之后,又从老墙深处传来了“布——谷谷”“布——谷谷”“布——谷谷”三声鸣叫,那声音几乎是我的复制,仿佛是我重播了一遍。显然,这三声已不再喑哑,完全摹仿了我的声音。我全身颤抖,热泪盈眶,几乎想从木格窗跳出去,奔向草丛,奔向那只灵性的布谷鸟。可是,我止住了鲁莽的举动,我的两手紧紧地攥住了窗棂。我生怕惊吓了这只孤独的生灵。 往后的日子里,那只布谷鸟依然是在早上推开窗子之时,还是往常的七声鸣叫,声音暗哑,低低的,幽幽的。到了关窗之时,仍是三声“布——谷”“布——谷”“布——谷”,它依然保持着自己惯常的一切。只是在这关窗的三声之后,我对着荒草的东南方向,合着它的叫声,再发出“布——谷谷”“布——谷谷”“布——谷谷”这样的三声,那只布谷鸟一定会很乖地发出同样的声音“布——谷谷”“布——谷谷”“布——谷谷”。它如我一样,那“布”与“谷”之间间隔长,“谷”与“谷”之间间隔短。它开始了与我的对话。从上次开始有了第一次对话,我就在心里给它起名“大神鸟”。它不是一只普通意义上的布谷鸟,就如同人类中的智多星、天才、高人一样奇异。 当我决定离开这座老屋,返回远在小城的家,这个念头是在薄暮时分起意的。可就在傍晚关窗之时,却意外地没有听到布谷的叫声。我对着窗外发出“布——谷谷”三声,布谷鸟一声未回。我又发出三声,依然是一片空寂。夜里,我望着黑漆漆的院子,心中涌起无限悲伤。是“大神鸟”知道了我的心思?知道了我将要离开这座小院?也许它真的知道了。因为我夜里爬起,对着窗外,无论怎样叫它,一直没有听到它的回音。空荡荡的夜里,只留下我的“布——谷谷”“布——谷谷”“布——谷谷”在草丛间荡着…… 本文入选《中国散文大系》《年山东作家作品年选》 时间深处的行走 一 时间是一位出世不久的幼儿,满眼新奇,满树惊喜。新奇和惊喜的嘴未等合拢,却又哇哇大哭。生长的疑问和时间的不确定,使得季节在安分守己的同时,制造着那么多未可知。时间不断更迭发芽,不断衰落繁华,刚刚还是漫天飞雪严寒刺骨,回转身却又大地回春暖阳升挂。并非天寒地冻满目荒凉,而是时间深处的行走,给了心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瞩望。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旷野中行走的,一路风景,让我经历着春夏秋冬。我的第一眼是深刻的,深刻至冬天里看穿一抹绿。我行走在风里,行走在风中的高速路上。阳光多么欢畅,欢畅的极致必然是鸦雀无声,阳光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给大地树木送来温厚的庇护。树木也学着阳光的样子,乖巧到无声无息地回报着一抹绿意。正值隆冬,干瘦的树枝是看不到绿的,没有绿的叶子和丝条,没有婆娑的绿荫和摇曳。可只要认真望过去,会发现,那抹绿,是藏在盎然的意图中的,在树干和树枝间,一路远眺,会看到朦朦胧胧的绿雾,罩在时间的建筑之上,淡淡然然,飘飘缈缈。天空压制了这种欢畅,用冷静的残酷和接纳的慈祥,背负起时间的行走。我不敢大笑,好似一笑,那抹绿会被吓跑。我不敢大哭,好似一哭,那抹绿会被剥夺生机,我只能在时间的纵深处行走,并与时间歃血为盟。 二 时间在行走中迷失了。我被劫持到一座荒岛上。这是怎样的一座荒岛。到处是风声厉厉,夜风哀哀。偶尔听到远处传来的狼嚎,夜色发出绿色的凶光。看不到人影,听不到鸟鸣,没有来与去的帆帐。只有四面的风声夹紧荒凉的嘶叫,逼迫茫茫的四野。白天和黑夜发出同一种颜色,从深渊发出的颜色。荒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星星,没有隐出月牙的迹象,太阳是早于荒岛的过客,被夜色早已吞没果腹。时间在荒芜里一再跌落,翻着惨痛的跟头,无力爬起。它努力挣扎,想在荒凉中扶起自己,却难以站立,难以抵御巨大的黑暗合围,黑暗,以无形的力量,压住天幕,压住时间的行进。一切在此凝固。死亡时时围追堵截着万物醒来。我从一个鲜花盛开的村庄,在一座清澈荡溢的天鹅湖上划着船儿采摘星星,突然就被一阵飓风劫持,裹挟着闪电雷鸣被抛到这里。恐怖的跌落,惊飞了心中的燕子,那曾经的呢喃,被摔成鬼哭一样的凄厉。时间横在岛上,做着破败的梦,在破败里,时间的荒目巡顾着荒芜的茅根,是否在野火烧尽后抽芽破土。 三 一只巫鹰飞在上空,我看不清它的面孔。它黑色的羽毛混合在巨大的黑暗之中。用翅膀扑棱着咒语,它说未来的天空下刀,地上长蒺藜,人类死后闭不上眼睛。我颤栗,我不想成为闭不上眼睛的其中之一。于是,我修佛,修善,修德,修行,我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我恪守一个幼儿的天真,我用白兰花罩护一双明净的眼睛,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场天灾人祸的劫掠。我像一个水缸被龙卷风旋起,以超速的声波旋于高空。在卷飞的途中,求生的本能始终扒紧缸的边沿,保持水流不被倾覆的姿势,并在惊恐万状中,仍然祈祷暴虐的风不要伤害了我的同类和亲人,我希望生灵不要受到惊吓,不要受到恶风的擦划。然而,再强烈的求生意念,再仁慈的祈祷,都没有逃过天灾的横行,最终,我的缸被时间毫不留情地摔地而碎,覆水难收。我开始醒来和死亡。当天灾过后的一片寂静浮现,时间开始了行走,在时间的行走中,我发现自己卷曲在一座荒岛上。我看到了一条通向时间的路,路的尽头是黑暗,黑暗的尽头是深渊,深渊的尽头是死亡。我正沿着这样一条时间之路行走,像我的缸,那些被碎掉的瓦砾。 四 时间无法沿时间之河溯流而上。我无法回到过去的时光。起初,单纯地以为是时间的错位,倒置了时空,想象着这是一场梦,梦中的惊恐与荒诞只是经历的一些场景。等梦醒来,就会回到现实。现实毕竟能寻到一份安宁,阳光,和鲜花的绽放,像我那个鲜花盛开的村庄,尽可以听到一片鸟语花香。可是,当梦醒却,醒后的一切却是黑暗密布,迷惘笼罩,时光的对岸已遥远得消失。我被时光之船绑架到了这样一座死角之岛。未等揭下蒙布,时光之船便一个闪电式回旋,就撤退得无影无踪。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那些黑色的恐怖、绝望的荒凉。黑暗里,我无数次伸出手,想抓住救命的稻草,然而,即使一段枯枝都难以捕食。这是一座没有生命的岛。来到这里,面临的只有等时间这把刀慢慢吞噬。起初,时间是一个振臂一呼万人响应的国王,当无数军队跟随征战沙场,时间是那么得心应手自得其乐。而当敌人大兵压境,士兵丢盔弃甲四处奔逃时,时间的国王暴怒而谩骂,它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惊吓和刺激,一改温善的面孔而翻脸成一个陌生的刺客。可是,当所有的士兵落荒而逃,只剩下国王孤零零一人时,时间的面孔由恐惧而变得悲哀和无助。我就是那个惊吓而暴怒、最后再也听不到哀号的那个奄奄一息的国王。我是时间的国王,我在时间中沦落为求生的乞丐。为了活下去,我开始在黑暗中寻找。寻找那座鲜花盛开的村庄,我童年的朋朋珍珍。 闭上眼睛,就能忆想上世纪那片烂漫的草坡,草坡上朋朋珍珍的身影,我用那些幼儿的稚声来驱赶身边冷嗖嗖的风,在心中燃起一支烛火取暖。童声刚刚咿呀响起,浓云却像山一样压过来。天幕四垂,万物悲催,黑暗围笼。时间的行走被一把大锁卡住了咽喉。 五 行走在时间的荒岛上,一切抗争无济于事。与命运的搏击,显得多么势单力薄。一棵鲜活的生命,于自然深处,面对风雨,已无缚鸡之力。生命的来与去,只能听凭时间的摆布。命运,像一个砥砺完美的魔术师,手中的魔棒操纵得如此变幻莫测,天衣无缝,以致于明知是在过愚人节,命运之神却笃愿被其蒙蔽而惊喜开怀。但是,繁华的背后,终有觉醒的声音。生灵在思考。那些失去热情和泪水之后的思考。 悲哀,无望,嚎啕,这些目光的形态,已跟随时间之王远征。荒岛之上,佝延着一只进化的动物。温暖与寒冷,白天与黑夜,欢乐与痛苦,渐失对比的敏感。即将面临的,或是枯枝的消失。对于一个站立、端坐、行走、躺卧已无界限的动物,任何姿势都不会起到有助于生还的意义。命运绳索被当成橡皮筋一样地游刃有余和轻描淡写。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放弃抗争的勇气。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意志。一夜白了头的人,还惧怕死亡么。一个被挟持的生命,流落成荒岛的土著野人,随时准备与荒岛一同赶赴沉于丘陵或谷底的命运。 但是,心有不甘的时间之王,却突然杀将回来,从远征之地风尘仆仆,一路披荆斩棘,杀声震天,一剑刺破天幕之湖,引来天上之水灌其铁树开花,枯木发芽。一夜间,太阳在黑夜劈开一道云缝。一丝光线,是射入荒岛的剑光。我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一只伏地的手从石岩下拖出,啊啊地向云缝打着哑语。我已失去语言,失去泪水,但,啊啊的手势,是羽毛生出的思想文字。硌嘭硌嘭的骨头,是我固体的泪。它们在一点一点蹦落出来,撒在荒岛的背上,向着云缝的光,像铁粒,叮当叮当招手。我固体的泪,在招手,朝着时间的王。 本文入选《中国散文大系》《年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声明:作品经作者授权发布,版权所有。欢迎分享,请勿擅自转载。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其他图片均来自网络。安卓用户可使用下方赞赏功能打赏,苹果用户可添加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nzizhanga.com/yzzpz/9049.html
- 上一篇文章: 词曲拔萃风冷停扇,蝉声渐断,奈何人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