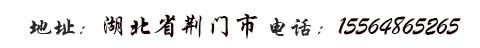华封三祝仰九如在这个中学里,他终日拿把
|
在温情多雨的江南,有一座的古朴而自得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北郊,有一所环境幽雅的中学。 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全国知名、才豪辈出的名校。盛产许多高考状元、奥数冠军和中学生比赛获奖者;拥有一批业界前辈、艺术大师和国家级优秀教师;也出了无数知名学者、政界精英和新经济商业大咖。网络上媒体上随处都是这所学校的痕迹:有校庆活动的盛况,有莘莘学子的情怀,有殷殷师恩的点赞、有郁郁校景的溢美…… 而我,只想说说在这所学校里曾经有这么一个少为人知的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数十年之中,校园里出没着他的声影,这个学校里他曾经好像无处不在;一甲子之后,岁月风干了记忆,校园里褪去了他的声影,一切依然,似乎又从未有过他的存在。 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普通的甚至没有怎么上过课,实际上最初他来到这个学校,只是负责在教务处刻蜡纸抄讲义的。他也许姓杨,也许姓张姓李姓一个很家常的姓氏;他也许有着一个很诗经很小雅的名字,也许只是被无知学生起哄者疯子癫子地乱叫。风过旧园,没有谁会特别清晰地去记忆一片落叶的形状。 这所中学规模不小,自然桃李满天下,而从年代到21世纪,凡出自这所中学的同学,提起这位老师印象都会很深刻;可是细细一想,也没有谁会对他特别有了解。他是这所中学里陈淤年代的一道永远风景,他也是这所中学岁月长河里的一尾过江之鲫。他来了,不为人知淡然而来;他离去,不为人知悄然隐去。 多少年来,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同学,提起他大抵都会会心地一笑:是呀,谁会不记得他? 每天清晨,他是个仪态儒雅的书生,在校门口不时来回散步,饶有兴致地呼吸空气,频频以谦卑的笑容和匆入校的学子打着招呼,满校园感染了他的快乐; 每天午后,他像个专业的园艺师,拿着一柄硕大的园艺剪刀,像绣花一样精心修剪着路两旁的冬青树,嘴里哼着歌曲,足下迈着舞步,满校园洒满了他的怡然; 每天黄昏,他行如神游物外的苏格拉底,时而仰天呼气太息,低头喃喃自语,似有解不开的情结,显得心事满腹,寂寥莫名,满校园弥漫了他的伤感; 他总是西装革履,但听说他从不洗外套,西装时间穿久放在床上压一压又穿上;他总是不和同事交往,但经常看到他追着学生硬要和人讨论问题:天南海北诸子百家天体力学水流径量;他总是游离在书声琅琅的课堂外,落寞在嬉笑打闹的操场跑道边,但常有学生不经意地撞到:在没有人的教室里,他一个人站在寂寞的讲台。在空旷的黑板前挥舞着双手,用标准洪亮的一口普通话或者用俄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讲的兴高采烈,面对着五十多张安静的座椅。像是陶醉地指挥着不存在的乐团,半眯眼睛,一脸幸福。 他常常关着办公室的门,独自在里面环抱空气跳着狐步舞;他常常就着同事的面织毛衣,织好了抽散,抽散了重织;他常常手里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棉鞋,面露温柔细细抚摸,眼神凝定若有所思。每当这时,他会向着对面的虚无温存呢喃,仿佛对面正有一个含羞怕惊的少女,这个时候他的嘴角会流露一丝微笑,那是一丝多么令人心碎的微笑。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忍心打扰他,别的教师会轻轻走远,替他赶开窗外不谙人事探头探脑想要嚣嚷的孩提。 显然,他是个有故事的人。这所学校出来的同学,多年之后也都会长大,都会明白更多的事理,想起他时,突然也会想到这一点:可是斯人早已远去,往昔只有片片鳞爪,再也无法拼出全图: 他建国初毕业于复旦大学,原为华东师大物理教师。学识渊深,任教用心。擅长朗诵演讲,能执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和西班牙语6门外语,六十年代因家庭出身不好,调至中学教物理。自此寂寂埋名,满腹经纶只是在和学生的嬉戏闲聊中偶露璀璨。终生落魄沉沦,终生未著一字。 他出自殷实门第,博学多才,为人谦和;他风度翩翩,出口成章,妙笔生花;他善音乐,爱跳舞,钟爱戏曲和绘画,能演奏手风琴钢琴电子琴口琴,甚至能织一手有漂亮图案的毛衣。他偶尔为学校出一期黑板报,精美的像西斯庭教堂的壁画,他的不世才气,却数十年只用在了拿着把大剪刀修剪冬青树,妆点大地生命的艺术。 他曾有一位同为复旦毕业的女友,心心相印,琴瑟相谐,然而造化弄人,不待结婚,女友不幸病亡。用情深切的他从此心怀郁郁,形单影只,甚至远远离开了主流社会,沉浸在自己回忆的世界里。那双女友做给他的棉鞋,被他视为珍贵信物,不管春夏秋冬,始终形影不离。他一直独身未娶。世间轻言天长地久,惟他真做到了生死不渝。 他似是不羁于世的外表背后,依然有一颗火热的拳拳之心。他曾经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他曾参与了新安江水库建设设计,他也曾和所有普通公民一样,沿着时代的足迹真诚信仰和本分奉献:参加兴修水库,筑防空洞,种试验田,种树绿化……那些青春悸动的往事,那些尘封在往事中的光耀,他从来不说。他一笑而过。 他尊重生命,热爱生活,他在这个功利现实的社会独善其身,坚守了另一个时代高贵的灵魂:博爱、从容、淡对世情,荣辱不惊。他甘愿俯下身子倾听孩子的干净的心灵,以一种外人看来像疯子的形态,固执地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他面对铺天盖地批判他的大字报还能平静地当书法欣赏;他一生之中只留下的寥寥几张照片全是灿烂的笑容;他的人格气度也许更能和另一个时代的那些我们神往的名字重合:胡适之、沈从文、金岳霖、钱钟书、陈寅恪……。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不要问我这是哪个城市哪个学校的哪位老师。是的我没说,是因为我不想说。他也许在这个城市那个学校,也许在每个小城每所中学,他是我们青春年少中的一份微细的记忆,几不可闻。他是我们温润社会中的一层浑厚风度,醇浓深远。知道的人不必多说都知道他,不知道的人无需多说不会知道。对,他就是你心中认为是的那位。 许多城市,许多中学,也许都有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年少的时候,见证着我们的生长变化,在我们记忆的另一边静静相随。我们也许从未注意,也许不经意地早已忘却,而他无论你记得还是忘却,静静地看你走过。犹如一张年代亘久而泛黄的旧照片,那一瞬间,时间静止。你在,他在。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发生在曾经?有多少人隐去了前身?有多少声音曾在空气中飘洒又慢慢飘散?有多少笑容曾在人群中灿烂又慢慢黯淡?时间会变成记忆,记忆会变成历史,历史会变成苍白。那个名字藏在心底却永生不提,那些故事不为人知却再也不说。 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在我们的记忆底层,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人:曾经静静地伴随你走过,如今天各一方杳无声息。他在远方,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你在这边,偶尔还会想到他吗? 附注一:年他因脑溢血离开校园,被妹妹接去了一座滨海的城市,后来他身体恢复回到古城,但年事已高不能再回学校了。他晚年生活平静安详,每天还拿起手剪修剪江边的冬青树。年去世。一生甘贫守简的他,临终时默默地给工作过的中学捐了十万元。他终老孑然一身,终身在心底铭记着那一个名字。 附注二:上元节到了。今天特地写了这篇,是为了纪念一个很多人久已遗忘的人,也是为了凭吊我们已然逝去的青春。写完文字,心里有点沉重。文字的背后,有很多无法形成文字的话。我只能在心里说给自己听。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许多人。 附录三:本文题目《华封三祝仰九如》中,用了“三多”和“九如”两个典故。“三多九如”合起来用也是一个成语,还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图饰的名称。“三多”、“九如”也常为后人取做名字。 “华封三祝”的典故出自《庄子?天地》,是一个成语,又叫“”三多之祝”是华州人对上古贤者唐尧的三个美好祝愿,这里是特以此典来表达往日学子对这位年颐德馨的老师的无限敬仰和殷殷怀念之意; “九如”的典故语出《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本为祝颂人君之语,后推而广之,泛指为祝寿之辞。现在这位老师已然作古,谨以此文遥祝他在天之灵安息,愿他和心爱的人终于相会,比翼长空。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nzizhanga.com/yzzyz/8188.html
- 上一篇文章: 人教三上三ldquo秋天的图画rd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