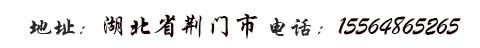辣椒燕子与双抢
|
烔炀河镇位于巢湖北岸的丘陵地带,七十年代,因人多地少,分到每个人头上的地仅有二分左右,且田块大小不一,不适合大面积耕种水旱作物,却也是江淮之间的鱼米之乡。那个年代,讲深挖洞广积粮,农业学大寨。春种秋收,烔炀镇四周是找不出一处闲田的。每年七月中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更是全镇农人每年必须经历的大考。这段时间,前后不过二十来天,社员们不仅一边抢收早稻及时晾晒,还要抓紧时间将晚稻秧在立秋之前全部插完,不然就会减产甚至绝收。为了能有一个好收成,社员们拼了命地和农时赛跑,所以叫“双抢”。 每年双抢,我的发小小娟家就紧张得不得了。小娟家和我家同住在镇上北垓一座坐东朝西的老屋里。我家住老屋前面一路屋,她们家住中间二路屋,蒋家住最后面的三路屋。 老屋后面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约二十多米的椿树,树冠将大半个院子都盖住,但它不是香椿,春天发芽的嫩叶不能吃,我们小孩子很不待见它,管它叫臭椿树。臭椿树上有一个大鸟窝,一年四季,只要我们“吱呀”一声推开院门,臭椿树上的灰喜鹊就“乌—-鸦,乌——鸦”惊叫,飞得树枝乱颤,树叶落了一地,叫声难听得很。我们顺手捡起一块瓦扎往树上投过去: “你们干了坏事吗,叫什么叫”。灰喜鹊倏地一下,飞到更高的枝丫上。 一大群燕子正在空中忽东忽西地捉虫子:唧唧唧唧——叽—— 似乎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查小娟大大(爸爸)是烔炀小学老师,大家喊他查老师,是吃公家饭的人,小娟妈妈是农业户。那时小孩们户口随妈妈,所以,他们家六口人有五个农业户口。 再过两天就双抢了,晚饭后,小娟妈妈端着小板凳摇着芭蕉扇,默不作声跟着一群社员坐到生产队队长家门口的场屋前。落座后,便一声不吭地摇着芭蕉扇。 小娟妈妈名字叫高翠华,常年穿一件蓝士林布大襟褂,黑布裤,黑布鞋。短发,高鼻梁,瘦长脸,一双深陷的眼睛经常无意识地淌眼泪。用奶奶的话讲:要是换一双蓝眼珠,怎么看都像法兰西人。廋廋弱弱身子,因听力不大好,我们平时总是要大声和她说话,她才能听得见。晚上,生产队长讲的话,也不知她能听到多少。 夏天,天黑的晚,队长吃完饭已经约八点往钟,西边的天还有一丝光亮。队长饭碗一丢,点根烟,便开始“双抢”动员。会议内容无非是动员社员们今年必须好好干,不能当逃兵懒汉。每家每户凡是有整劳动力的必须参加。生产队会每天下午给大家伙儿送绿豆汤和大西瓜。双抢工分比平常干农活多加两分工,干得好工分多,秋收不但稻子分的多,说不定生产队上缴公粮后的粮食款也能分几十块钱。 小娟家平时劳动力只有小娟妈妈一个人,到了双抢,整劳动力就变成三个。小娟大大、妈妈和小娟锅锅(哥哥)。其实,小娟大大是师范毕业,正儿八经烔炀小学老师,并不是生产队社员。但每年这个时候,生产队是不讲这些道道子的。小娟哥哥虚十六岁,在烔炀中学上初中。因双抢时间正好赶上学校放暑假,那就躲不掉了,是真的要出力的。 烔炀河镇上其他人家,凡是农业户,也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能算整劳动力的一律算上。小娟在家老二,比她哥哥小八岁,算不上整劳动力,她下面还有五岁的二妹查小妹,三岁的小妹妹查小宝,皆是少不更事,需要查小娟帮着爸妈照顾。 不需要参加双抢,小娟便负责在家洗衣烧饭喂猪,活也不轻地很。 天朦朦亮,头没梳牙没刷,小娟已经将大锅灶里的山芋稀饭烧开,再塞两个草圪蹴进锅洞,让粥嘚浓一点焐着。再从大腌菜坛子里,将去年冬天腌的冬腊菜拿出两捆,洗、切、炒。拿一个大窑锅乘起来,放在锅台子上,用木盖子盖好。就抓紧将泡在大脚盆里全家衣服,在搓衣板上打上肥皂使劲搓,挤出乌黑带着泡沫的水后,沥水抮干放到竹篮里,拎到镇上西边的电灌站上引水干渠里垂打漂洗,莫约一个多钟头后赶回家,到屋后面院子里将衣服在铁丝凉好。这个时候,小娟妈妈、大大和泉水锅锅已经从田里回家吃过早饭,又回田里干活了。 刷牙梳头,回到锅灶台边,将锅里剩下的粥扒了两口,洗锅刷碗。再用升子从米缸里舀两升米倒进淘米箩,右胳膊上挎着淘米萝,左手拎着空丝蓝,丝蓝里放着一把镰刀。先上菜园摘菜,再到查家坝淘米洗菜。这个时候,奶奶怕小娟一个人忙不过来,允许我再挎着一个丝蓝帮小娟到菜园摘菜,米和菜洗干净后,帮小娟一起烧饭。 小娟家和生产队其他社员家的菜园地,皆临近镇东边,查家坝边上的一片河滩地,地势不高,有烔河从边上蜿蜒流过。河滩南边是成片稻田,高高低低的,再往东就是烔炀河镇东边的东绵山。 屋外,阳光白煞煞的,小娟和我眯缝着眼往菜园走。菜园四周,晚稻刚刚插下去,细细的秧苗似站在一片片水汪汪镜子里,远看是雾蒙蒙的嫩绿。田里的水映着天上流动的云,时不时有雪白的稻鸡从田上飞过。远处,东绵山连绵起伏苍翠蓊郁。风吹过,空气里有好闻的野月季花的香,田埂上带露珠的青草撒发阵阵泥土的气息,吸一大口,醒脑,人也立刻高兴活泛起来。 夏天的菜园是一年四季里花样品种最多,长得最茂盛的时候。一路穿行过去,一双双韭菜、萝卜、瓠子、葫芦、丝瓜、黄瓜、菜瓜、苋菜、辣椒、茄子、南瓜、豆角像是早晨洗了脸小伢,清清亮亮。风吹过来,瓜菜叶子们高高兴兴地在风中摇曳,沙沙沙地,引得鸟儿虫儿青蛙蚂蚱蜻蜓蝴蝶翁翁翁地忙来忙去。每隔几塽菜地,都会有一个沤粪大缸撒发大粪发酵臭气,因是露天,并不觉得那么难闻。几个轰鸟用的稻草人,带着破草帽穿着破衣服,站在菜塽子上,喝醉酒似的瞎晃荡。 在菜园地里穿行,我忍不住在小娟前面大喊: “小娟,你看这家的西红柿长得真好,红彤彤,不想吃,也想把它们摘下来。黄瓜长得肥嘟嘟,好馋人呢”。 小娟忙说:“二姊,不能摘哦,人家看到要讲话的,那就好丑哦”。 我咧嘴笑:“嘻嘻,我吓唬你呢”。 走到小娟家的菜园,打眼望去,四五陇菜地,只有茄子,西红柿,豇豆,冬瓜,茼蒿和辣椒几样,没有人家的菜地一半热闹。别人家菜地是花红柳绿,他们家菜地是人瘦毛长,无精打采。仔细看,青茄子没长大,西红柿大小不一,泛着青黄,没有红。冬瓜也伏在土里只有香瓜那么大,能够摘得只有茼蒿和辣椒。辣椒是整整一大双,从头到尾差不多有农村一间厢屋那么大,茼蒿有半个双子。 割了一篮子茼蒿,再摘辣椒。小娟家的辣椒真是与别人家不同。人家辣椒可能粪水施的足,个大肉厚,果实饱满,壮壮实实,躲在辣椒叶子底下,闪着碧绿碧绿的光。小娟家的辣椒倒好,光辣椒杆就瘦个郎精,长的辣椒也大小形状不一。大的矮爬爬地像个扁灯笼,小的尖嘴猴腮讨人厌,更多的是干巴巴的辣椒拗子,几乎每个辣椒都有虫眼。 我忍不住抱怨:“小娟,你妈妈栽的辣椒苗不好吧,怎么个个都像丑八怪”? 小娟伸腰抬头望着菜园,像是自言自语:“菜园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忙,她天天还要到生产队上工,家里菜园就忙不过来了。我家大大和锅锅又在学校教书的教书上学的上学,帮不上我妈妈”。 我还是忍不住说:“我家奶奶讲得对,你家大大就是不晓得惜顾你妈”。 “怎么搞呢,我家妈妈跟大大吵过好多回,没用。二姊,别看我家辣椒长得丑,但辣得很,下饭”。 小娟望着远处,闪着一对乌亮亮眼睛笑眯眯叮嘱我:“二姊,摘辣椒最好别将辣椒扭碎,不然辣椒汁炸到手上,火辣辣的疼,二三天都不好过呢”。 太阳高高挂在天空,刺得人眼睛睁不开。我们抓紧时间将茼蒿辣椒拎到查家坝里清洗。小娟说:“二姊,我妈妈讲,我家辣椒太小,介个就不要将辣椒连籽带把充掉,只要将辣椒把子摘掉,里面的籽不去,回家用刀背将整辣椒拍碎用蚕豆酱炒着吃”。 我和小娟站到查家坝的青石板上,水刚刚摸到小腿。小娟用手将篮子里的辣椒在河里轻轻划几十下,待水清了,再用力上下冲橦十来下,算是清洗干净。我也顺手将装茼蒿的篮子浸到水里使劲划,水清了后,再拎起丝蓝上下橦十几下,茼蒿和辣椒就基本干净,拎回家,再用井水冲一冲就可以下锅炒。洗完菜,我们便急急忙忙往家赶。 烔炀河人家的大锅灶均有两口锅,一大一小,大的用来炒菜煮饭,小的用来烧喝的开水。小娟先将洗好的茼蒿和辣椒炒好,我帮小娟烧火。因为是双抢,小娟往锅里倒的香油(菜籽油)比平时多一点,待锅里菜籽油冒青烟时,倒入茼蒿快速翻炒二三分钟,用大窑锅将茼蒿盛起。从烧水的小锅里,舀一瓢水倒进大铁锅,干丝瓜瓤子一涮,再用抹布擦干净,接下来炒辣椒,小娟将这些活干得熟练地很。 锅烧热,到香油,油热,倒入辣椒。刺啦一声,哎哟,可不得了,通前到后三路老屋,到处弥漫呛人的辣椒味,呛得人眼泪鼻涕一大把,大咳不止。小娟和我实在受不了,辣得跳出厨房门外。奶奶在前面屋里闻到了,拖着一条残疾直腿,站到天井当中,一边咳凑,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使劲抱怨小娟妈妈:“这个翠华啊,真是不顶龙,种这么辣的辣椒,辣死人了”。 小娟和我听了,笑出声。小娟拿出另一个窑锅盛辣椒,往锅台上一放,用袖口擦着眼泪,对站在天井里的奶奶哆囔:“三奶,是滴嘛,不晓得怎么搞滴,我妈妈种的辣椒就是比别人家的辣椒辣好多,有时吃饭,辣的我都咽不下饭”。 莫约快一点钟光景,小娟饭煮好了,三菜一汤。一窑锅清炒茼蒿,一窑锅蚕豆酱炒辣椒,另一个窑锅冬腊菜,外加一搪瓷盆蚕豆瓣鸡蛋汤。 我家屋里的座钟噹噹响了十三下,奶奶说:“小娟,你大、你妈怎么还不回来”? 说话间,说曹操曹操到,小娟妈妈、大大和泉水锅锅戴着草帽拿着镰刀从大门进来,顿时,一股热熏熏的风也跟着一下子扑进堂屋里。人还没进大门,小娟大大就高声大嗓,夸张地拖着长音:“娟子啊,娟子哎,饭可好了唼,累死了,累死了噢,饿了饿了噢”。 小娟脸上挂着汗珠子,拿碗筷答应:“大大,饭烧好了哦”。 大门外面又一前一后进来二个小人儿,哼哼唧唧,一路哼进屋:“大姊,大姊,饿死了,饭可好了唼,哼哼哼,我要七饭”。 是小娟的俩个妹妹,查小妹和查小宝。个个都是一副哭丧脸,小脸晒得通红,身上好多红疙瘩,因戴着草帽,捂出一头汗,站在小娟身边,烦躁地抓耳捞腮。小姊妹两个,每人手上拎着一个篮子,每个篮子里都是从河滩割的猪草,是给家里唯一的猪吃的。 小娟妈妈,大大和泉水锅锅三人放下镰刀,赶紧在天井里将大椋子的井水搲到脸盆,浑身上下一路擦泥擦汗,最后,再将一盆浑水往泥脚上使劲一冲,抓起大茶缸凉茶一顿咕咚,坐下缓口气,没人接小姊妹两人的话。小娟一一将饭盛好放大桌子上。 小娟大大端上碗扒拉两口说:“怎么一点肉都没有”? 小娟妈妈放下碗筷,用手抹一把擦眼泪(小娟妈妈有常年无意识流眼泪的毛病)答:“哪有钱”? 小娟大大:“前俩天不是找张老师家借了两块钱吗”? 小娟妈妈答:“不是买盐、酱油、称了两斤猪油炼油了吗?这大热天不七点猪油腿哪有劲”? 小娟大大:“那找三奶借两块,明天称毫肉喰,这么热的天,七不好,要出人命呢”。小娟妈妈根本不接她大大的话,低头扒着碗里的辣椒就着米饭。 屋外,炙热的太阳烤的天井的青石板滚烫,小娟、小妹和小宝三姐妹扛着碗,赤脚跑到我家的堂屋里闹门子,一屁股歪到小竹椅子上吃饭。查小妹端着碗吸着脓鼻凑到我跟前抱怨: “二姊,就我妈妈嘛,天天让我们七茼蒿,我一七头就晕,我妈妈还讲我好七嘴馋”。 我说:“我也是,不晓得怎么搞得,我也是闻见茼蒿一股药味就头晕,根本七不下”。 恰巧,小娟妈妈也端着碗到我家堂屋吃饭,听了查小妹叽叽喳喳,也擦了一把眼泪,嘀咕一句:“我今天七了茼蒿也头晕,也不晓得怎么搞滴”。 小娟接着她妈妈的话,带着哭腔:“你就知道种辣椒,我们都七辣死了,你不能种一点别的菜吗”? 小娟妈妈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喊:“全家就我一个人做事,要忙得过来哎,挡炮子子的,一个都不帮忙”! 小娟不说话了,知道妈妈在骂她大大。因为小娟知道,大大从来不会主动帮妈妈干农活。她大大喜好吹拉弹唱,喜欢人家喊他査先生。最喜欢帮人家写信,写字,和人打牌,要是镇上有什么文艺活动,他一定带着二胡热心参加。小娟大大是个好老师,但对农活实在不在行。 奶奶从屋里的碗橱里,将我家中午留的半窑锅渣肉(米粉肉)端出来,先给小娟妈妈挑两块最大最好的,再将其它夹精带肥的一人两块分给三姐妹。三姐妹眼里放着光,狼吞虎咽地闷头吃饭,半盏茶功夫,一大碗白米饭下肚。下午三点半,生产队长哨声响起,小娟妈妈、大大和泉水锅锅拿起草帽镰刀和水壶开始下午的收割。 柳树上的蝉一天比一天叫的欢,狗整天伸长脖子留着哈喇子,鸡也张着嘴到处找水喝,天像一口烧热的大铁锅,烤得人无处躲藏。参加双抢的人开始还有劲咒骂老天,骂着骂着就不作声了,头扎着顶毛巾,迎着烈日扬场晒稻谷,擦一脸汗珠子,抬头望天,暗自祷告,日他妈妈的老天!什么时候能打一场暴唼,双抢再不过去,就要出人命了哦。 小娟妈妈瘦小的身子更加黑瘦,背更驼,眼泪流的更多。泉水锅锅因天天穿着白背心割稻,前胸后背晒了脱皮,红皑皑一大片红痱子。小娟大大也晒得黑炭一般,天天不停地喊累死了累死了,搞得小娟妈妈既委屈又伤心地向我奶奶诉苦。说小娟大大懒得拖蛆,人家男人不都是这么干嘛,挡炮子子的,就他累,我们都不累吗?每当这个时候,奶奶不仅借钱,还天天帮小娟家收晒在后院子里的衣服,叠好交给小娟。奶奶要是煨了瓦罐肉汤,总要留一碗给小娟妈妈。泉水哥哥及小娟三姐妹也时不时尝到奶奶平时舍不得吃的苹果、饼干和糕点。实在没什么吃的,奶奶还将饼干桶里锅巴拿出来,每人泡一碗麻油锅巴解馋。 眼看着双抢进行一大半,一天清早,小娟妈妈带着小娟锅锅从屋后院子里拿一根长竹竿到外面,穿过老屋过道时,竹竿不知怎么将老屋中间屋梁上的燕子窝带掉了一个,这下可闯了大祸。 中午,小娟在锅灶里烧火,小娟妈妈从田里赶回来烧菜,差不多有百十只燕子黑压压站在小娟家老屋的屋梁上,黑背白肚黄边嘴,齐刷刷站成两条直线,张着大嘴一齐冲着小娟妈妈:叽叽叽叽——叽--,唧唧唧唧-唧--,燕群激奋,一边叫一边不停摇头摆尾啄来啄去,甚至还冷不丁从高高屋梁上突然一个俯冲,快要到小娟妈妈头上了才又一转身飞回屋梁上叫骂不停,声音大得人面对面讲话都听不清。 小娟家老屋梁上有两个大燕子窝,每年开春燕子都回来做窝,过小燕子。燕子是益鸟,我们一路屋三户人家都很喜欢,人鸟一屋和谐共处,大家都很高兴。今天这是怎么了,引得燕子这么凶,发这么大的脾气,冲着小娟妈妈大声喊叫。 我一溜烟跑到屋梁下看着义愤填膺的燕子,不解地问小娟妈妈:“小娟妈妈,今天燕子怎么搞滴啥”? 小娟妈妈炒着菜叹口气:“介个早上抽好空闲,我跟泉水从后院子里拿长竹竿到菜园搭豆角架,不小心将屋梁上一个燕子窝碰碎了,找我们赔呢”。 呀,抬头一看,是滴,屋梁上是少了一个窝。 小娟坐在锅槽里烧着火,望着她妈妈,一脸担心:“妈妈,燕子生气了,明年不到我们家做窝怎么办”? 小娟妈妈答:“我喊你大大找人在屋梁上再搭个窝,这小东西真不能得罪哦”。 奶奶不知什么时候也过来看热闹,抬头手搭在眼帘上,陪着小心跟燕子说:“小伢们哎,不要吵了,翠华家不是故意的,明天我让他们做一个更好的窝给你们住,介个就不要吵了噢”。 奶奶真诚地陪着笑脸,双手又是作揖又是打拱。小娟妈妈也再次走到屋梁下,冲着燕子拱手赔笑脸:“那个啥,你们行行好,是我们的错,介个下午我喊人帮你们把窝补好,是我们不对哦”。 燕子们好像听懂了似的,又唧唧唧唧喊了一个钟头,大部分燕子纷纷离去,剩下的燕子似乎也喊累了,进窝里歇息,好不容易安顿下来。 “哎哟,我的妈哎”。小娟跑到我家堂屋,小声对我说:“乖乖,燕子吵起架来好凶哦,总算让我妈歇一口气。我妈现在找我大大去了,说下午找人来做个一模一样的窝。我妈说不想明年燕子不到我家来”。 奶奶在一旁用篦子篦着白发,说:“是呢,可不能让燕子离窝”。 天天割稻拔秧插秧,小娟妈妈、大大,泉水锅锅累得精疲力尽,小娟大大除了抱怨还是抱怨,小娟姊妹三个也因没有人管,也越来越瘦黑。尤其是三岁的查小宝,每天吃的饭食和大人一样,青菜、豆角和辣椒,偶尔西红柿蛋汤、蚕豆蛋汤,或小娟大大借钱称斤把肥多瘦少前夹肉,和萝卜一起烧一大锅解解馋。因缺少营养,喝了不卫生的水,查小宝小脸上常年长一块块白色的虫斑,头大身子小,瘦黄瘦黄,像个绿豆芽。 这天晚上,小娟妈妈、大大、锅锅吃完稀饭,又上田里去了,查小娟也跟到田里帮忙,家里就剩下查小妹和查小宝姊妹俩。查小妹洗碗扫地喂猪。查小宝因为这几天不舒服,看到晚饭又是炒辣椒和稀饭,绷不住大哭了起来,因为辣椒实在太辣。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连忙回屋告诉奶奶查小宝不舒服。奶奶摸摸她的头,没发烧,说小宝是热的,没胃口,辣椒不要吃了。奶奶从碗橱拿出一瓣冰镇西瓜,小宝吃了又要昏昏欲去,我连忙喊查小妹帮小宝洗洗澡让她先睡觉。 月亮已经挂到西边,天不早了,奶奶这几天也是因天太热也不舒服,连吃三天香茶(中药)。她嘱咐查小妹帮查小宝洗澡,便早早回屋睡下,我也瞌睡连天,跟着奶奶进屋睡觉。谁成想,小娟妈妈他们四人从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四点才回家。 泉水锅锅第一个发现查小宝端着半碗辣椒粥坐在天井青石上,背靠着竹凉床睡着了,一脸的灰。查小妹一个人睡在另一张竹床上,两人身上都被蚊子咬了一身红包。 泉水锅锅心疼地大喊:“嗷嗥,小宝怎么睡在地上唵?一把抱到凉床上”。小娟大大心疼地说:“乖乖,你怎么搞的哎,一身包哦”。一摸头,还好不发烧。 我也被他们吵醒,揉着眼睛跑到到天井,看着一身红包的姊妹俩不知说什么好,小娟妈妈和小娟忍不住眼泪一把把掉...... 哎,要人命的双抢,什么时候才结束哦...... 很多年过去了,年冬至,我和弟弟陪父亲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小娟、泉水锅锅一路陪着我们。在通往公墓的路上,远远看见查小宝一路小跑,边跑边对我喊:“二姊,二姊,我早就跟我大姊讲了,从小就阿姨(我母亲)最心疼我,今天做冬至,我一定要跟阿姨打声招呼说说话”。 远远望去,查小宝穿着一件红色羽绒服,系着红围巾,瘦瘦小小,扎着马尾辫,像个小姑娘。其实,小宝的女儿都已经上大学了。我十二岁离开烔炀河,一晃三十多年未见过查小宝了。老远地,我拖着长音喊:“查-小-宝,快-一-点”! 不知怎么,心头一热,喉咙哽咽,禁不住噙着泪,什么话也讲不出。当年那个脸上挂着眼泪,端着一碗辣椒粥,歪倒在天井青石上睡了一夜的小姑娘,早已经和故乡一起,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 下午返程,车一路西行。弟弟默默开车,父亲闭目养神。车窗外,高高低低的田畈里,稻桩若列队的士兵,披挂厚厚的霜,矗立凛冽寒风中。一眼望去,禾田已经干涸,咧着枝丫一样口子,枯白静气。田块若一幅幅大写意水墨泼画,横亘在巢湖岸边。一条细细小河上,有三五鹭鸟轻盈飞过。太阳早早挂在西天,微红的光晕透过厚厚的云隙,映在山丘、小河、田畈、菜畦与蜿蜒公路上。远处,田野上走来一晚归的农人,披着黑色罩衣,抽着旱烟眺望着远方。一张风霜雨雪侵蚀的脸,透着宽厚澄净安详。不时闪现的农屋窗户里透出橘色柔和的光。远远地,又仿佛看见寒冷的冬夜里,母亲在煤油灯下,用剪刀为呱呱坠地的查小宝剪脐带,满手血。转眼,人生四季走得那么急促,昨日还是鲜花着锦美树浓阴,而今却已秋风乍起风萧水寒,永不再来的少年时光。 作为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四季轮回?四季转换也是一种哲学启示吧。春天象征蓬勃的少年时期,走到哪里都是活扑扑的,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无来由的轻盈欢笑,可肆意挥霍可铺张。青年时代是盛夏,处处大树美荫,枝叶丰满,呼来喝去,应有尽有。生命到了秋天,才真正安静下来,半生精力用尽,也是最绚烂的时候,也最短暂,一忽儿用完了,迎来漫天落叶,这个时候的生命,就像脱衣服,一件一件,最后剩下肌理和骨头。走到晚年,就是走到皑皑白雪的寒冬,山河大地,处处铁画银钩,鬓发悉白,一步一步走向永恒的归宿,长睡不醒......不远处有哭声隐隐约约,再回头,看人世间风雨如泼,心如刀割。 人们啊,从远古匆匆走来,又匆匆离去,未曾停息,也永不停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 今日天气潮热,湿度大,上午瓢泼大雨 修改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anzizhanga.com/yzzgx/8240.html
- 上一篇文章: 敦煌,一只燕子古今放歌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